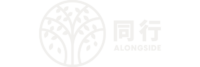生命足跡:表達藝術治療及預設醫療指示工作坊,為配合預設醫療指示(AMD)的立法及推廣,同行 Alongside 推出一連串公眾教育活動,透過講座、工作坊及峰會等多元形式,讓不同背景的大眾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及其對醫療自主的深遠意義,推動每個人都能以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。
當「不救人」才是真正的「最佳利益」:醫護人員與預設醫療指示的抉擇
徐子健醫生|同行 Alongside 共同創辦人
03/08/2025
當「不救人」才是真正的「最佳利益」:醫護人員與預設醫療指示的抉擇
《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》將於 2026 年 5 月正式生效,為「預設醫療指示」(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)和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」(DNACPR)訂立法律框架,讓成年人可於仍有認知能力時預先表明:在特定情況下,自己不願接受維持生命治療。
這個法例的出現,為不少醫護人員帶來新的挑戰與思考—如果我根據病人的意願停止治療、甚至移除維生系統,那麼我是否違背了「救人為本」的醫護專業精神?
這樣的疑問是可以理解的。在學習和訓練的過程中,多數醫護人員所接受的教導,就是如何把握每一線生機、如何延續病人的生命。然而當面對「預設醫療指示」這樣一個鼓勵尊重個人選擇的新法例,或許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: 什麼才是真正的「最佳利益」?
什麼是病人的「最佳利益」?
對大多數人來說,「救命」似乎自然就是對病人最好的安排。當我們因突發事故或重病送院,大家都希望醫護團隊全力搶救,讓我們回復健康。這種情況下,積極治療無疑符合「最佳利益」。
但當情況改變呢?
假如一位病人已長年受病痛折磨,藥石無靈,生活質素急劇下滑,甚至連基本溝通與清醒時間都不復存在;如果此人早已在神智清醒時清楚表達,不願意在失去意識後被插喉、心外壓、依靠機器延續生命,那麼「繼續生存」是否仍然是病人的「最佳利益」?
事實上,「最佳利益」從來不是只有一個固定標準。它應該是根據病人當下與過往的身體狀況、疾病預後、痛苦程度,更重要的,是病人本人的價值觀與意願。當一個人清楚告訴我們「我不想要這樣的活著」,我們是否還應強行延續他的生命?這樣的堅持,是關愛,還是折磨?
尊重選擇,也是一種照顧
在我們日常生活中,個體的選擇受到高度重視,無論是求學、工作、戀愛、搬家,旁人可以給建議,但最終決定權屬於自己。那麼,當一個人面對生命的盡頭,為什麼不能也擁有同樣的選擇權?
預設醫療指示所強調的,不是「放棄治療」,而是「預設界線」,在無法自主表達時,也能夠按照自己原本的意願被對待。這是一種對人生的負責,也是一種人性尊嚴的延續。
醫護人員或許會覺得違背「救人」的天職。但我們想邀請大家思考:
也許「幫助病人完成他的選擇」本身,就是一種最深刻的照顧。
醫護的角色:從搶救生命,到成就選擇
《香港醫務委員會專業守則》中指出,醫生應根據病人的「最佳利益」作出醫療決定。這樣的專業責任,從來不是單靠延續生命去衡量,而是應該包含對病人選擇的尊重、對他們人生價值的理解。
當病人透過預設醫療指示,清楚地表明不希望在某些情況下接受維持生命治療,醫護人員依照指示行事,並非放棄病人,而是履行另一種形式的專業照顧,以尊重與理解作為基礎的臨床判斷。
我們理解,在執行病人意願的過程中,醫護人員可能會感到不安,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違背了職業初衷。然而,只要我們重新思考「最佳利益」的真正意義,便會發現:真正的醫護精神,不止於救命,而在於尊重與陪伴。
在Alongside,我們常常與面對疾病、衰老、離世的人同行。這些歷程讓我們更加相信: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計劃自己人生終章的權利。而醫護人員,是協助實現這份終生自主的守門人。尊重病人的預設指示,不是退讓,而是用專業成就他人生命的完整。